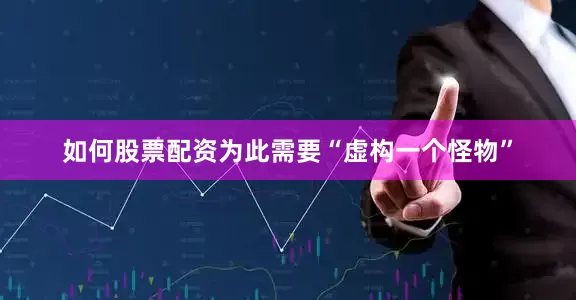图片来源:a16z
本期《Upstream》对话 Roy Lee——Cluely 的联合创始人,也是当下最“出圈”的 Z 世代创业者。他的故事堪称反传统:从接连被哈佛、哥大被开除,到靠一个 AI 面试“作弊工具”做出 2.5 亿次曝光的爆款原型。
这位曾因使用 AI 工具在技术面试中作弊而被哥伦比亚大学开除的年轻人,如今正以一种极具挑衅性的方式重新定义科技创业的范式。他不相信“产品-市场匹配”是第一性原则,反而主张“传播先于产品”,将情绪引爆、内容分发、舆论操控作为增长的三段式引擎。
他认为, 在一个基础模型飞速迭代、产品生命周期被极度压缩的时代,传统以产品为中心的增长逻辑已经崩塌,而能掌握算法节奏、制造话题争议、驾驭社交平台传播链条的创始人,才是真正的赢家。
他要做的,是一款“半透明 AI 覆盖层”——一个能读屏、能听声、无处不在、但始终隐身的智能接口。这不仅是一种产品形式,更是一场对传统软件交互范式的挑战。在 Roy 的世界里,创业像直播,融资像造梗,用户获取靠的不是 SEO,而是 meme 供应链。你可以讨厌这种方式,但你无法忽视它的效率。
展开剩余95%这期节目,像 Roy 本人一样,充满分歧、争议、爆点与未来感。如果你还用传统方式判断一个 AI 产品值不值得投,这期对话会让你彻底失去“专业幻觉”。
从被哈佛开除,到做爆TikTok的创业者
Erik Torenberg:Roy,作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人,你现在感觉如何?
Roy Lee:前几天我们发布了公告,很多人喜欢,也有人讨厌,更多人可能是中间派。反应真的很疯狂。你想想,六个月前我还只是个宿舍里的普通大学生,而现在,我感觉自己站在了科技世界的中心。更疯狂的是,我对“病毒式传播”这件事的判断居然完全命中。我越来越觉得,像Twitter或LinkedIn上的科技人群,其实整体是滞后的。而那些真正理解Instagram、TikTok等平台算法的人,很少会同时了解这类“tech Twitter”的世界,这两个圈子的交集非常小。我基于这一点的预测,就自然成立了。看到它一步步发生,真的很疯狂。然后Elon出面说要10亿美元收购Cluely,Brian还开玩笑说,“千万别这么干。”当然啦,我们的口号就是 “To the moon, to the moon”(意思是直接冲上天,像币圈那样暴涨、彻底爆红)。
Erik Torenberg:Roy,这真的太精彩了。我记得你在官宣前24小时就把视频发给我,说:“兄弟,就是这个了。”我当时看了就觉得,“好吧,这绝对行。”但我没想到它能火成这样。
Roy Lee:我完全没预料到它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,也确实低估了大家的正面反馈。现在网上已经出现了各种关于我的meta分析,有些甚至挖得非常深,做到两三层的结构。我看到一篇文章,把对a16z的meta分析和Cluely关联起来,说什么“思想结构的可互换性”。说实话,我完全不明白他们在讲什么。但这些做“文学评论”的人真的很厉害。不是开玩笑,真的有人写了一整篇分析,认为a16z的思想框架可以直接套用到Cluely上,甚至提出我们背后有一套完整布局,a16z想统治整个赛道。我的反应就是:拜托,别这样,真的,别这样。我们这边是在下一盘包含四十步的复杂棋局,而他们却在解读什么“左手握手”的象征意义。兄弟,冷静一点吧。还有人在Twitter上发帖,说跟Brian聊到了什么。我当时差点回一句:“你对Cluely的看法,其实是你对自己的情绪投射。”但最后还是删了那条推文。我不想在Twitter上激化情绪。我可以在播客里表达观点,哪怕最后被剪辑传播出去。但我不希望主动制造对立。
Erik Torenberg:你现在身处的这个位置,其实可以从你的童年到现在找到很多线索。你觉得自己从小到大有哪些一以贯之的特质?
Roy Lee: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引人注目。从小学到初中、高中,总有一群人很喜欢我,也有一群人很讨厌我。我永远是那个最大胆的,脑子里想到什么就直接说出口,从不设防。这也导致我很极端,要么特别受欢迎,要么特别惹人讨厌。这种状态在我高三那年到达了巅峰:我学习成绩很好,很早就被哈佛录取,但我一直在做各种疯狂的事。比如我偷偷溜出学校的实地考察活动,晚上过了宵禁还在外面,最后是警察把我送回去的,当时已经凌晨两点了。我们那时候才十六七岁吧。后来我就因为这事被停学,然后有些“反Roy阵营”的人开始大肆举报我,最后哈佛把我开除了。从那之后,我就开始了创业之路。我那会儿的想法是:我要在创业这件事上干出点名堂。这个转折实在是太疯狂了。你看,我爸妈的公司是做大学升学咨询的,教别人怎么进哈佛,结果他们自己最小的儿子被哈佛赶了出来。这简直是“招生咨询行业最大危机”。
所以我们决定低调一点,反正我的分数成绩都还在,也许明年申请另一所学校也能进。我就这样在家待了一整年。我低估了那一年的精神折磨程度。我可能是你见过最外向的人,基本没办法连续八小时不跟人说话。但那一年我必须自己一个人待着。这让我开始思考:既然我的人生已经这么离谱,不如把我的疯狂信念翻倍,加倍去做最有趣的事。那一刻,我决定我要全力投入创业,没有任何退路。我根本不可能去干别的事。
Erik Torenberg:我本来以为你会在那之后变得更谨慎一些,想说“是不是得收一收”?但你反而选择了完全相反的方向。
Roy Lee:对,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,而且我知道事情最终会往回走。你想想,你独自在一个房间里待了整整一年,没人跟你对话,你最疯狂的想法开始变得合理,你脑子里全是自己的声音,就像一个回音室一样,它把你的一切想法都放大了。这正是我成为现在这个自己的原因。而我愿意为这个自己下注。后来,我在父母的压力下去了加州读社区大学。加州就像一个缓冲区。在加州,我既能尝试创办公司,也能完成亚裔家庭对教育的期待。我那时告诉自己要去哥伦比亚大学,至少去一个学期安抚父母。我到了哥大,第一件事就是想找个联合创始人和一个老婆,这两样是我在大学最想要的。老婆我还在找,但那天我遇到了Neil,我的联合创始人。我们开始做各种项目,唯一跑出来的,就是Cluely的最早版本。
Erik Torenberg:那你父母有没有试图去“改造”你?还是他们后来也接受了“Roy就是 Roy”这件事?
Roy Lee:在我考进哈佛之前,他们是天天想管我。但当我成功拿到录取时,他们突然安静了,觉得“哇,这孩子真的做到了”。然后我被哈佛开除,他们又变得很生气,直到我去了哥伦比亚,他们才又重新觉得我很厉害。他们就像:“他居然能再进一所常春藤,我不敢相信,但可能他那些不按常理出牌的操作真能打出本垒打。”
Erik Torenberg:你之前说过,你爸妈不管怎样都会爱你。但我很好奇,他们现在是怎么看待你的?他们还会担心你吗?
Roy Lee:哥大之后他们完全松懈了。真的很夸张。比如我现在跟我妈说:“我要辍学去做这件事。” 她就会说:“哦,好啊。”
Erik Torenberg:就像她早就预料到一样。
Roy Lee:对,还会问:“你怎么没早点辍?”我说服我的联合创始人和我一起退学花了挺长时间,但我妈基本上已经支持我做任何疯狂的事了。
内容先行,产品其后:病毒式传播的新逻辑
Roy Lee:我们可以从Twitter或类似的平台聊起,讨论下内容策略是怎么演变的。这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,比如YouTube刚作为一个平台出现时,那是个转折点。它基本上让内容实现了民主化。你不需要再为商业广告付费,传播力和知名度也不再取决于你在电视或广告位上投入多少钱,而是由内容本身的质量决定。五年前TikTok 出现,短视频算法开始主导一切,再次改变了框架。现在的问题不再是“你能不能做出好内容”,而是“你能不能做出足够多的内容”。因为平台上根本没有足够多的好内容供大众消费,这就是为什么你会不停刷到那些无聊的滑稽剪辑、重复的Minecraft跑酷视频,只是因为没别的内容可看。
但有两个关键点很多人没意识到。第一,你只需要制作那些大众愿意消费的内容。大多数人其实不知道怎么做病毒式内容——能让任何人看得懂、愿意点开、看得完的那种内容。总有一部分人想当“最聪明的人”,写一些全世界只有200个人能读懂的深奥内容,然后希望别人觉得他们很有思想。他们确实表现得很深思熟虑,但这根本不具备病毒性。第二,算法现在真的会放大最有争议的东西。我之前在Instagram和TikTok上混了十年,非常清楚什么样的争议内容会爆。我知道你需要适度“越界”,踏入那个有争议的灰色地带,内容才会被疯狂转发。
LinkedIn会爆,是因为它的算法极度偏爱这种东西。它会把这些内容推送到每个人的动态里,即使观众还没准备好。但我做的事情,就是把IG和TikTok上的争议性原则直接复制到 X(Twitter 更名后的新品牌名称 “X”)上,而他们完全没意识到。我之前说过,这可能是我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。而我敢说,我的视频在IG和TikTok上不会像在LinkedIn上那样火,唯一的原因是它们还不够有争议。现在有些人在平台上明示自己在犯罪,或者至少暗示自己在做违法的事,但观众还是只会说:“OK,bro。”这还不够吸睛不够疯,远达不到“有趣”的门槛。X上的创作者也还没意识到——现在的内容生态缺的不是聪明才智,是“争议性执行力”。
Mark有时候会说,模因传播就像供应链一样,听上去很荒诞,但他说得没错。模因从Reddit出发,然后进X,接着流入Instagram,再到LinkedIn,最后登上CNBC,就像一列车。有些人确实晚了,但如果你能把真实性和争议性融合推进去,就可能操控整个链条。有时候,这条传播链甚至从4chan开始,然后Reddit、X、Instagram、LinkedIn,一路顺延下去。对我来说,一切都是从Instagram起势,但Twitter在“疯狂”的程度上往往比其他平台更早爆。
那些在X评论区里觉得我太极端的人,如果让他们花一个小时浏览我的Instagram主页,他们的大脑可能直接烧掉。他们完全无法理解,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在大规模地消化这种内容。而这恰恰是因为,自从Elon接管X后,平台的争议性就更大了。有人会抱怨说太极端、太负面、太黑暗……但这只是开始。这就是内容的未来。你不会再看到什么千禧一代创业者了,接下来是Z世代的创始人全面登场。我保证,他们跟我一样,成长环境一样,对内容的理解也一样深。我像一只金丝雀,提前把风吹出来了,但我可以告诉你,这波潮流才刚开始,而且是不可逆的。你要做的,就是接受它。
Erik Torenberg:你是怎么意识到,分发渠道本身是一种稀缺资源的?你又是怎么把“做传播”这件事,和一家真正的科技公司结合在一起的?
Roy Lee:是在我第一次走红的某个时刻,我意识到自己知道一些别人还没弄明白的事。就像我掌握了一种算法语言,但前LinkedIn用户还不懂。而一切最早开始于一个叫“面试程序员”的项目,那其实就是Cluely的原型。我用它在Amazon技术面试中作弊,之后我把它开源发出去,结果上了各大科技公司的黑名单,也被学校开除了。那件事本质上就是病毒式传播的教科书案例。你想,历史上有谁因为作弊被常春藤大学开除后还拿到500万融资?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。
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是可以重复构建的东西,但在后来的视频发布中,我对“病毒感”产生了直觉。我会整天刷Twitter,想:为什么没人做Avie Schiffmann做的那种事?为什么没人照做?后来我做了“招50个实习生”的项目,结果也炸了。我开始持续性地做病毒视频,直到某个时间点我意识到他们没抓住“精简算法”的精髓,而我抓到了。结果就是,我的视频能主导时间线,不只是几天,是几个月都在刷屏。而他们还停留在过去,不肯也不敢跟上来。
这就是我招50个实习生的逻辑。你在公司里要么是工程师,要么是创作者。就两种角色——要么构建产品,要么产生影响。我定义的“创作者”,标准很明确:你至少要在一个社交平台上有10万粉丝。这是你真正掌握病毒传播能力的唯一证明。如果一家公司有营销团队,但CMO连10万粉都没有,那这家公司就应该换人了。游戏规则已经变了。
Erik Torenberg:所以你觉得这种“实习生 + 内容军团”的策略,是其他公司也应该采用的范式吗?
Roy Lee:完全应该。我之后会再详细说说实习生的事儿。我们当时发了一个视频,宣布要招50个实习生,视频火得不得了。这些实习生整天的工作就是:做内容。我们现在有超过60名内容承包商,按视频支付报酬。他们的工作内容就是:坐在镜头前拍TikTok和Instagram视频讲Cluely。这就是现在的营销。这份工作在五年前是不存在的。你怎么解释一份工作,它的核心是:坐在镜头前做5个10秒视频,然后这些视频看起来毫无意义,却能持续带来几百万的播放量。这份工作听起来一点意都没有,但——这就是我们的现实。
募资、爆红与势能:当分发成为护城河
Erik Torenberg:实习就像是现代营销实习的升级版。我们为观看量支付的费用非常少,而与此同时,其他公司,比如你们,为了一则超级碗广告要花上几百万美元。但你用两万美元就能获得相同质量和数量的曝光。你觉得这些曝光能转化吗?
Roy Lee:是的,当然。我们的转化主要来自我们在Instagram和TikTok上发布的视频。
Erik Torenberg:说到这儿,我们也该让Brian来聊聊了。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?你和Roy的合作关系是怎么一步步建立起来的?我挺好奇这个故事的。
Brian:我也很高兴能和你聊聊。我是在纽约认识Roy的,有个朋友叫Ali Dvau,她总是混迹在年轻人聚集的地方。有一次她发给我一份名单,上面有Roy的名字。我看了看他在做的事,感觉很有趣,有点像童子军那种真实感的边缘探索。我就联系了Roy,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,我当时发消息说,“嘿,听过你的名字,咱们应该聊聊。”结果你回我说,“哥们,我们可以聊聊。”但没过多久你又发来消息说,“其实你是 multi-stage,我不想跟你说话。”你还补了一句,“我顾问说我们不该聊,别来烦我。”
我当时也可以就此放弃,但我说,“好吧,我们不谈融资,我只想和你聊聊,建立个关系。”谢天谢地你同意了,我们简单通了个电话。你讲了你的起源故事,我当时心想:“哇,这孩子太有意思了。”虽然你不接受投资,但我还是继续关注你,看你的推特,追踪你搬去旧金山之后的动态。后来我不知怎么搞到你的电话号码,就给你发短信说,“我在你办公室楼下,能见一面吗?”然后你说:“好啊,上来吧。”就这样我去了。我记得那天刚好有个工程师也是看到你在Twitter或Instagram 上的内容,就直接上门来找你,虽然彼此完全不认识。
还有个朋友Nicolas当时也在你那儿。整个场景非常特别——一群人在创作内容,你和Neal在开发产品。那个时刻我感觉,“OK,这地方真的在发生一些很特别的事。”我就想,“我们得回来。”再下一次我去的时候,我带了一些东西过去。你正在吃牛排,还给我展示一些你们的指标和数据,我意识到你们真的能把“关注度”和“眼球”转化成收入。你会说,“哦,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营收,有企业客户来找我们……”我当时心想,“天啊,他真的把流量变现了。”而这在很多创作者那里是完全做不到的。那时我正在写关于“Momentum”(势能)的文章,我的观点是:在AI这个赛道里,要突破噪声已经难到几乎不可能,尤其是做ToC产品。但你却做到了。我当时的判断是——能持续掌控舆论节奏、懂得构建分发机制的创始人,会成为最终的赢家。
所以后来我们推进得很快。我记得当时我们让你点一点链接,上传Stripe数据,然后就说,“好了,我们不再多问了,咱们聊聊吧。”后来我们一起做了一场很酷的采访,还和你的一些合伙人聊了聊。你之前还打趣说他们都“又老又秃又无聊”。我们很兴奋能促成这笔交易。我记得我人在拉斯维加斯的LP峰会,还特地打电话给你谈条件。然后,我还送了你五六磅牛排。你特别兴奋,我也决定加倍下注,继续保持这股势头。
Erik Torenberg:那你是怎么意识到这个“势能”可以作为一种策略,尤其适用于AI公司?这个理论是怎么来的?它到底意味着什么?
Brian:我其实一开始并不觉得“姜饼策略”有效,也不认为“势能”是护城河。我以前更相信工匠式的产品——那些真正打动用户、留存率极高的产品。我当时最关注的就是产品的留存率、有没有网络效应,那种传统的护城河逻辑。
但随着移动互联网成熟,很多产品形态都被尝试过了。我开始意识到,更重要的是找到用户愿意反复使用的产品。而当AI出现之后,我仍然抱着这个思维框架:找出那些能不断高留存、高复用的应用。但现实是:底层模型更新太快了,几乎每周都在变化。你今天好不容易构建出一个漂亮的产品,明天可能OpenAI就更新了模型,或者某个新能力完全颠覆你设计的逻辑。所以我们不能再做那种“慢工出细活”的产品,而是要做创始人能非常快速出击的产品,同时还能理解“分发”机制的本质。AI的能力太魔幻了,根本无法预测,我们就像是在建一架已经坠崖的飞机。那些在飞机下坠时还在兴奋建构的人,才是下一代的赢家。
半透明覆盖层:重新定义AI的使用体验
Brian:说到像Roy这样的人,他们属于那种能迅速捕捉价值、充满激情,并且在节奏上始终走在前面的少数人。他们能将分销、营销与产品构建三项核心能力整合在一起,从而打磨出一款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、具备长期留存力的产品。在我看来,最理想的产品,是用户愿意每天打开、长期保留的那种工具。不过我们现在仍处于AI的早期阶段,很多产品和能力尚未稳定。在这个阶段,“势能”才是真正的护城河——掌握注意力节奏、快速试错、快速迭代,远比传统意义上的“技术壁垒”更具决定性。
回到Roy身上,我很想听听你自己的看法。我们私下聊过你产品路径的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,也反复谈到你所强调的分销优势。现在也许X和LinkedIn上的许多人还没完全理解你到底在做什么,但我相信,随着时间推移,这种理解差距会自然缩小。Paul Graham在创办Y Combinator时曾经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洞见:技术创始人其实一直被严重低估。在过去,很多人以为创业必须是MBA的事情;但Paul发现,教会一个技术创始人如何经营生意,其实比教一个MBA如何打造产品、写出好代码要容易得多。而且随着AWS、低代码平台、AI工具等基础设施的演进,过去十五年里,“做出一个产品”这件事本身变得越来越容易。但与此同时,分销却日益稀缺。软件已经供过于求。
正如你在文章中引用Andrew Chen所说:“所有的营销渠道都已经烂透了。”每一个渠道都越来越无效,变得乏味、疲软。在这种背景下,创始人不只是技术或产品专家,还要像“受众联合创始人”一样,深谙如何在注意力争夺战中脱颖而出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像MrBeast、Kylie Jenner这样的内容创作者,开始打造自己的商业品牌。比如MrBeast的Feastables、Kylie的美妆线。这些人确实掌握了大量注意力,也做成了消费品牌。但你会发现,他们打造的大多是实物商品或DTC品牌,而不是软件产品。
Justin Bieber曾试图推出一个叫Shots的社交平台,John Shahidi也借助他的影响力尝试过其他项目。但真正成功地将“创作者身份”与“软件公司”结合的例子,几乎没有。目前的大多数头部创作者更擅长经营品牌,而不是构建SaaS或面向C/B端的大型软件服务。我有时会想,为什么MrBeast不直接去做一款像Square那样的产品?他明明掌握着全球最大的注意力池,按理说完全可以将流量转化为一个利润更高的工具型产品,甚至可能比像Fastables这样的项目更成功。他现在也在做游戏,我认识他,真的很厉害。但我最欣赏Roy的一点是,你真正把“创作者”和“软件创业者”这两个角色结合了起来。你不仅掌握分发节奏,还能做产品迭代,真正实现了内容与工具的闭环。所以,要不你来聊聊你反复提到的分销策略?也顺便说说,从产品诞生到现在,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化过程?
Roy Lee:其实很多人不知道,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行代码是10周前才写出来的,Cluely真的是个非常新的项目。最早它的前身叫Interview Coder,是我在宿舍里花一个周末写出来的。当时这个产品就是一个“面试作弊工具”。我们用它做了一些测试,没想到一下子就获得了2.5亿次展示。我们意识到,“哇,这么多人会对这种体验产生兴趣,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款更通用的工具?”我们感觉自己在用户体验上确实做出了差异化,那就也许能基于同样的体验赚更多钱。
所以我们就把它扩展成Cluely,本质上就是把Interview Coder的原型推广到所有场景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通用的作弊工具,是一个隐形的AI覆盖层。我们做的其实就是重新定义AI的用户体验,然后推给尽可能多的人,看看会发生什么。结果呢?Cluely的总浏览量已经超过10亿次,我们可能是目前全球传播速度最快的初创公司之一。而且我们手里还有所有使用数据,它们告诉我们——“嘿,这里是问题最难、最需要关注的地方”,这其实直接引导了我们后续的产品方向。
分销能力强大的最大好处是:你根本不用担心产品的市场契合问题。因为用户的使用数据会自己告诉你,他们需要什么。如果你没有这些数据,那你就是在盲目摸索,任何创过业的人都懂这种感觉——你根本不知道产品该往哪走。但如果你分销做得足够好,其实你也不用反复问用户,你只需要看他们在用什么,看总体的使用量。这相当于你可以重新定义 MVP 的意义。传统公司可能需要几个月来构建一个新产品,再观察用户行为。但我们可以用更快的方式测试一个想法,只要你能起草一个有趣的点子、快速发布,就能立刻验证它是否真的打动人。
比如我们发布最初那个视频的时候,产品其实还没真正ready,前一天我们刚刚通过最后一个测试,就说,“差不多可以了,我们先发视频看看。”结果视频一出,立刻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用户。我们甚至尝试在视频里加入了一些针对销售场景的暗示,想看看大家会不会用它来打 sales call,毕竟这是个利润高的领域。结果短短时间内,我们就从那些做销售电话的用户那里拿到了超过100万美元的企业营收。这感觉就像你在黑暗中试图射中目标,但我们现在的方式可以更快、更准确地预判传播效果。你不需要做百万次产品迭代分析,因为算法已经能告诉你答案了,那个答案就是——观看次数、点赞数、分享数。而且这种测试方式非常简单:你不需要先定义“市场契合度”,而是先看这个视频、这个内容有没有“病毒契合度”。这其实是我们策略里的核心点——由用户数据引导产品演化,而不是假设需求去构建。
Brian:对,你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点我们内部也讨论过——形式因素。你看Roy,可能是世界前1%的那种人,既懂怎么构建产品,又知道怎么结合内容和分销机制,构建“venn 图中心”的创始人。像你设计的那种“半透明 AI 覆盖层”——听上去很简单,技术上其实也不复杂。但这种组合方式很少有人能想到、并真正执行得漂亮。正是因为这点,我对你们在做的事情感到非常兴奋。我自己现在也在用Cluely。
打破专业幻觉:Z世代创始人的内容范式
Erik Torenberg:构建这个功能时,你是怎么思考“防御性”的?尤其是从用户角度来看——他们的规模。OpenAI也在布局分发,对吧?你怎么看这件事?
Roy Lee:是的,我们是第一个切入这种全新用户体验的人。我们真的实现了“半透明覆盖”这种体验。人们迟早都会接触到这种“半透明层”,它才是真正“集成人工智能”该有的样子。就像苹果演示的那种“液态玻璃”那就是未来AI的形态。现在这就是一场土地争夺战。我其实完全不担心分发问题,关键就在产品质量。说白了,这真的就是一场土地争夺战,看谁能更早说服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和企业,让他们相信你是那个该赢下“半透明覆盖层”的人。我们已经制造了那么多噪音,既然“半透明覆盖”是未来的标准,那为什么不是我们来主导?
Erik Torenberg:你是什么时候发现“半透明覆盖”是正确方向的?
Roy Lee:我记得那时我和Neil还在宿舍,我们每天都在琢磨怎么让“面试程序员”变得更隐形。我们大概做了二三十个版本,最初其实都不太行。,它就是给你一道编程题的答案,然后你要把它“覆盖”在自己的代码上。但我们后来发现,我真的想把它直接集成到我的代码里,我要看到自己写了什么、AI给了我什么。最后我们落在“半透明”这个方案上,我们都惊了——“哇,这才是产品该有的样子!”很快我们意识到:为什么只考虑“编码面试”这个场景?软件工程里的编码面试,其实是个特别小的市场。而这种模式其实适用于所有事情。AI不应该像一个独立的窗口,它应该无缝集成在用户正在操作的界面中,而且以“半透明”的形式存在。
Erik Torenberg:我想让你聊聊你是怎么考虑“分阶段推进”的。
Roy Lee:现在网上确实有很多声音在问,“产品呢?产品在哪里?”但我们每天都在夜以继日地打磨那个存在于我们脑海中的产品。用户不断告诉我们他们想要什么。其实我发的每一个和产品本身无关的视频,都让最终的产品发布变得更有热度,我敢保证发布那天绝对爆火。我知道很多人都强调“尽早发布”“快速上线”,这没错。但当我们真的大规模这么做时,大家却说,“哦你们太早发布了,现在怎么办?”但我们写第一行代码也就10周前,比最新一批YC公司还早。
整个产品从开发到现在也不过两个半月,我们目前还处在一个预发布阶段。而这种大规模预发布的最大优势在于:你能尽早验证用户真正想要的产品是什么。如果我们能向数百万用户传达“这个产品就快上线了”,他们就会形成明确的期待。我们已经在全网大声喊出了这个信号:AI覆盖来了,它能看到你的屏幕、听到你的声音。既然如此,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做别人的产品?从第一天开始,甚至在正式上线之前,我们就不断地发声、造势。这个阶段的核心就是分发——要把Cluely这个名字深深刻进每个人的脑海里。Cluely是什么?是看不见的AI,它能看到你的屏幕、听到你的声音。等我们真正上线的时候,还有谁不会下载它?
Erik Torenberg:你做的事情很有趣。我会把它和我们TBPN的朋友类比一下。他们最近重塑品牌,明确地称自己是“企业支持的媒体”,因为每个人都说自己是“独立媒体”。他们说:“不,我们是企业驱动的,这样更诚实。”他们有自己的风格和幽默感。你也一样——你主动靠近争议,甚至把争议变成了一种策略。虽然有些人觉得那是假象、是刻意为之,但你做事的方式真的很真实。人们觉得自己认识你。即使你塑造了一种角色,有时甚至带点夸张,但某种程度上,这种真实感是存在的。
Roy Lee:是的,我也觉得这其实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一种变化。过去几十年里,“专业化”正在快速下滑,而一个关键原因就是:内容创作被彻底民主化了。YouTube上那些最初的创作者,很多就是在宿舍里拍搞笑视频的人,那才是真实。人们渴望这种真实感,他们已经不想再看广告、不想再看企业宣传稿了。他们想看的是“真实的人在做真实的事”。而现在,这些真实的人能被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观众看到。但直到今天,几乎没有公司真正理解这一点。很多传统品牌的账号连基本的影响力都做不出来,他们只会说“我们有个发布会”“我们上了个新品”,但内容完全没观点、没个性、企业气息十足。
相比之下,大家更愿意看到一个极度透明的世界,连创始人也必须是诚实的。我们想做的Cluely,从来都不是一个广告,而是某个人的生活故事,它是真实的。我一直在努力做到比硅谷99%的公司更透明。当然,这种透明也带来一些代价。确实有人会因此感到不适。我听说有人把我们这种方式称为“RZ营销”——算是一种略带讽刺的恭维。他们说,“我讨厌这种RZ营销”,因为他们更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所谓的“产品基本面”上。但我想说,这种方式本身就是我们Cluely的基本面,也是今天这个时代的运行方式。所以我常常开玩笑:那些想要干掉我们的人,也许真能“干掉我”,但他们杀不死这个想法。我们创公司的方式,会影响下一代。我们还在早期,但即便只是激发了一点点转变,也很有价值。
Erik Torenberg:你刚才提到“病毒式营销”,但我听你之前说更愿意把它叫“反脆弱营销”,能解释一下吗?另外你觉得从过去那些最具争议的事上,你真正学到了什么?
Roy Lee:“反脆弱营销”对我来说是更贴切的说法。因为每次当我制造争议,就算有人来砍我,也会有三种人冒出来:一个讨厌我、一个支持我、一个保持中立。这就像你获得了更多的“光环点”,可以说是一次“光环耕作”。至于你问我学到了什么,我的答案很明确:永远不要去打击别人,也不要靠近打击别人的边界。我发现算法确实在奖励“真”。它也奖励其他很多东西,但“真实性”是最被奖励的。我有时会在X上发一些很真诚的评论,比如“谢谢你,我真的很尊重你。”我发现人们真的很喜欢看到这种表达。你可能看到我对Gary Tan的回复,那是真的。我尊重他。我希望有一天,当公司达到我设想的高度时,他会认可我们。我不认为教训是要“对一切三倍下注”。真正的教训是:如果你足够诚实,算法就会奖励你。现实中,几乎没有公司能在每一件事上都百分百诚实,也很少有创始人能始终真诚待人。Elon Musk是唯一的例外,他确实在商业世界里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。
Erik Torenberg:你觉得你们的用户,会在意你们这种极具个性的表达方式吗?像那些特技视频、小短剧,怎么看待它和用户之间的关系?
Roy Lee:很少人会真的在意这些内容是不是“专业”。四十年前,工程师们还在穿西装打领带上班,否则就会被觉得“不专业”。现在却反过来了——如果你穿西装,反倒会被认为“太刻意”“太做作”。大家现在追求的是真实。但社会上仍残存着一种观念:公司必须“品牌友好”、不能说任何有争议的话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会变成一种社会规范。但现实是,人们真正想要的是“有趣的东西”。这才是生活的意义。你看短视频平台的崛起,大家每天都在刷最离谱的内容,早就审美疲劳了。
这也是为什么像“精子竞速”这种运动会突然走红。十年前你根本不可能在CNN上看到这种内容,但现在谁还需要CNN?你有Instagram,有TikTok,它们就是喜欢“精子竞速”,而且真的有机会变成一个合法的新型体育项目。不仅是“精子竞速”。现在每家公司都在谈Sam Altman怎么通过GPT时间线引爆全球热度,Elon Musk也因为政治立场频繁成为话题中心。企业正变得越来越有争议,也越来越“不专业”。这种趋势不会很快消失。而我,就是那个挑战这些边界的人。也许我比现在这个世界准备好的程度还要超前一点。
所以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:你能想象Cluely真的赢了,会发生什么吗?如果我们成功地向全世界证明:“这就是新时代的专业主义”,那不仅是美国,整个全球的企业文化都会随之改变。大家会意识到:我们过去在“品牌”与“专业”上的所有担忧,其实都是错的。这个世界真正渴望的,是不一样的东西。我始终相信我的判断是对的。我在X和TikTok上的判断就是对的。我一直不明白,为什么没有人去拍那些明显为算法量身打造的视频。可能只是因为没人愿意按下那个按钮。但我按了。如果Cluely真的赢了,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?你可能会更感兴趣:如果每一家公司都实现100%透明,都去做最有趣的内容,那世界会变得多么有趣?就像Elon Musk说的——最有趣的结果往往最有可能发生。
Erik Torenberg:这是与Roy Lee和Brian一起完成的精彩一集,非常感谢你们参加这期播客,感谢你们的到来,谢谢!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BR1-JrGbwxY
编译:Nicole Wang
欢迎扫码加群参与讨论
--------
发布于:浙江省股票怎么买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